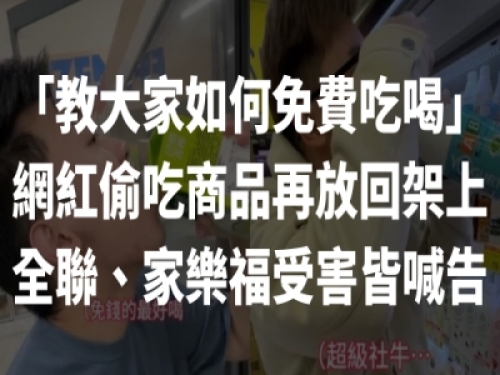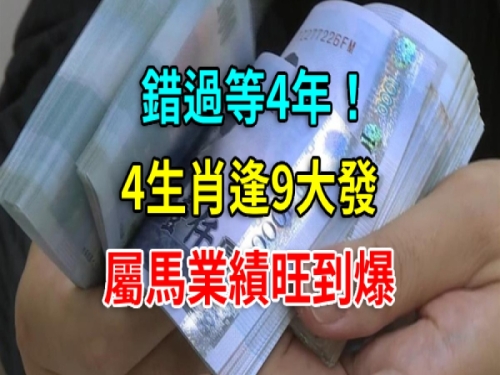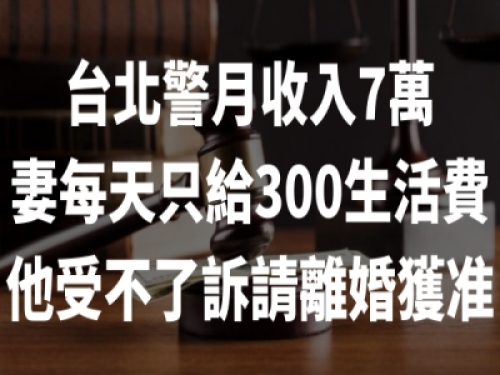電影「長城」除了帶給我們娛樂效果外,還有什麼隱藏的內涵價值?《長城》﹕中國文化的世界表達

近日﹐由張藝謀導演的電影《長城》在北美3326家影院大規模上映﹐在海內外引起熱烈反響和討論。去年﹐該片在國內上映時﹐獲得了11.68億元的票房成績。從國內到海外﹐電影《長城》不僅在全球電影市場競爭中獲得了機會﹐更帶著濃鬱的文化特色向世界展示出中國的精神風貌。隨著《長城》的海外熱映﹐人們再次將目光聚焦於這部電影。光明日報特約請兩位專家撰寫了評論文章﹐從電影產業﹑文藝創作等角度﹐解讀該片的文化內涵和市場價值。
工業試驗與藝術創新
隨著電影《長城》在北美上映﹐張藝謀及其電影再次成為電影評論的風暴中心。作為“第五代”導演的佼佼者﹑中國式大片的開啟人﹑奧運會開幕式導演﹐張藝謀多重身份的交疊使其在輿論場中的位置備受矚目﹐甚至無形中背負了中國文化代言人的角色。這種全能印象招致觀眾對《長城》的落差批評。但事實上﹐《長城》作為一次合格的向好萊塢工業藉水行舟的試驗﹐無疑是張藝謀職業生涯裡一次重要的創作博弈。
新世紀以來﹐華語電影工業版圖重繪﹐進軍好萊塢的華人導演屈指可數﹐張藝謀是大陸第一位與好萊塢達成A級商業類型片合作的導演﹐《長城》也是迄今體量最大的中美合拍電影。作為傳奇影業籌備了7年的項目﹐英文劇本署名五位作者﹐七易其稿﹐實拍三年﹐團隊裡有超過百位奧斯卡級別的獲獎者和提名者﹐特效更由頂級的“維塔工作室”和“工業光魔”協助完成。作為中國電影人才和資本與好萊塢電影工業的一次深度合作﹐《長城》更像是張藝謀在當前中國電影產業化轉型語境下深入好萊塢體制的一次探索。製片權力和文化輸出的主動優勢成為中美雙方在合作過程中持續博弈的焦點。
張藝謀在《長城》中被壓制的創作權力使其區別於以往的作者身份指認。好萊塢的工業標準大幅限制導演權力﹐從這個角度來說﹐《長城》作為好萊塢的重工業產品﹐本身就是去個性化的。個人的美學旨趣需要在嚴苛的製片人制度內尋求突圍。張藝謀也坦言在製片過程中自己能掌控的東西有限﹐《長城》必須首先是合格的好萊塢工業產品﹐在這個前提下才能承載中國文化和價值輸出。這種矛盾突出表現在影片敘事層面的艱難對接﹐西方視角﹑故事簡化﹑人物性格缺少弧度﹑風格元素奇觀化等都是本片招致批評的原因。但在有限的敘事空間裡﹐張藝謀依然在好萊塢的框架內對集體意志與個人價值﹑男女主角的情感勢差以及中國精神之於人物性格的呈現作出了平衡和提昇。同時﹐張氏影像風格在《長城》中仍清晰可辨。影片將東方人工奇跡與西方魔幻類型相嫁接﹐張藝謀在怪獸片的框架內與好萊塢討價還價﹐盡可能多地配置填充精奇的中國元素﹐承續中國風表達。影片藉助長城這個典型的中國舞臺﹐展示出科技感十足的古中國特種部隊﹑奇巧的冷兵器戰爭場景和頗具視覺壓迫性的饕餮獸群﹐工業技術指標和視覺效果呈現皆堪稱近年華語電影突出的國際化嘗試。敘事薄弱和高度奇觀化是高概念電影的一大“原罪”﹐本質上是在面向全球市場的生產傳播中﹐文化勢差和資本風險所致的保守創作行為。高概念電影力爭在文化折扣最低的代價下盡可能地打通市場﹐藝術家的自我表達不是其必備要素﹐藝術創新也不能作為其唯一評價指標。這是文化工業的普遍矛盾﹐傳奇影業近年出品的怪獸電影代表作《環太平洋》和《哥斯拉》在劇作和風格上同樣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責。
即便如此﹐高概念電影仍是當前電影經濟文化輸出的強大載體﹐也是國家電影工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2016年中國電影市場增速放緩﹐電影產業面臨轉型壓力﹐亟須對產品結構優化調整﹐實現向質量型增長的過渡。近年“中國式大片”式微﹐以超級英雄電影為代表的好萊塢大片已然佔據國內主流市場﹐中國電影僅靠中小成本的“黑馬”創造票房奇跡並非長久之計﹐中國電影產業想要建立完善的工業模式﹐必須保證高概念電影的競爭力和傳播力。《長城》作為中美深度合作的第一部超級大片﹐由中方主創直接向好萊塢取經﹐借鑒工業體系﹑製片模式和技術標準﹐將促進中國電影與好萊塢在重工業層面的深度交流合作﹐進而提高中國電影的工業水準﹐成為重建中國大片模式的契機。
《長城》的全球化市場定位不言而喻。當前中國電影因文化和語言上的障礙﹐與海外尤其是北美市場的對接是短期內難以完成的任務。《臥虎藏龍》和《英雄》之後﹐華語電影在世界主流市場的影響力持續走低﹐缺乏進入好萊塢主流市場的話語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好萊塢高概念電影持續將中國作為超級英雄獲得神秘力量或是科幻對壘戰場的景觀想像﹐甚至推出“中國特供”版來討好市場。在此背景下﹐《長城》藉助好萊塢體系植入英語創作﹐讓東西方文化話語體系在電影中直接對話﹐減少與外國觀眾的隔閡﹐尋求共同認可價值觀的努力﹐也是一種全新的嘗試。電影摒棄了中西文化的衝突和對抗﹐在好萊塢敘事法則的主導下﹐盡可能地通過中國元素來影響敘事﹐嘗試進行價值觀的反向輸出﹐試圖以“信任”為立足點在中西方文化間找到價值認同。“減法”操作雖然削弱了劇作張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嘗試了中國集體主義美學與西方個人主義價值的對接﹐這種主流價值觀的交流﹑融合和輸出﹐也是中國電影“走出去”的重要命題。在這個意義上﹐《長城》承載了中國電影海外文化傳播的探索意義。
創作層面的博弈對應的也是電影工業和市場的博弈。中國電影市場良好的發展前景無疑是好萊塢主動尋求《長城》項目合作的直接動力。中國電影面臨對好萊塢進一步開放的嚴峻挑戰﹐中國電影產業也將進入全球電影市場格局的競爭﹐如何在與好萊塢的對壘中保持本土電影的創作優勢和市場份額將是未來博弈的關鍵所在。從這個角度看﹐《長城》開了一個好頭﹐接下來還需中國電影人的共同努力。
信任的力量
張藝謀執導的電影《長城》裡雖有諸多明星參演﹐但最重要的角色依然是張藝謀本人。所有的毀譽依然集中在他的身上。這一次﹐張藝謀無疑又給了我們一個“現象級”的作品﹐在中國電影市場增速放緩的時候證明了自己的票房能力。他讓“長城上打怪獸”的戲言變成了一部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電影﹐並試圖在這部好萊塢工業化流程之下生產出來的奇幻大片中加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傳達。張藝謀擅長使用的那些巨大的象徵符號﹑宏大的場面和瑰麗的奇想似乎都用上了﹐給我們講述了一個看起來是歷史﹑但完全“超歷史”的想像故事。正像這部電影開始時特意向我們說明的那樣﹐這是關於長城的“傳說”。這樣的設定﹐時代背景雖模糊﹐但脫離了具體歷史時間的限制﹐用超歷史的玄想隱喻對這個世界發言﹐形成了一個以商業模式來傳達文化意味的範本。
當然﹐《長城》最引人注目的是好萊塢怪獸電影那種“重工業”的強烈氣息和張藝謀慣常使用的中國傳統文化內容和藝術意象之間的對接融合。這種視聽效果的營造﹑故事的打造和明星的創造無不深刻顯示著這部電影的全球商業背景。這是擁有最大的潛在觀眾群體﹐並且已經在全球電影市場上凸顯了自身巨大影響力的中國電影和有著強大技術和成熟創作積累的好萊塢的一次直接對話。該片各種高技術的充分應用﹑跨國團隊的使用和全球電影人的協作﹐讓這部電影有了一種“跨國性”。這既是一種超越﹐也是一種開拓。張藝謀在其中試圖將中國傳統文化的意味傳遞出來﹐確實是一次非常具有探索精神的嘗試﹐其難度之高﹑風險之大﹐可想而知。
這裡的怪獸雖然有了來自中國神話傳說的名字──饕餮﹐但這些漫天遍野﹑無窮無盡的狂野動物﹐是和中國文化相異質之物。它們沒有任何自我﹐不能凸顯任何個體性﹐祗是無窮無盡的野蠻﹐向著可怕的毀滅一切的目標奔馳﹐而文明人難以防守它們瘋狂的攻擊。無可控制﹐吞噬一切的“饕餮”﹐當然是這個世界上不可控的邪惡的某種隱喻。張涵予所演的老殿帥的死亡﹐劉德華所演的軍師和鹿晗所演的士兵都死於和饕餮的悲壯戰鬥。而這些戰鬥的力量﹐來源於技術的發明﹑發現的不斷更新及文明所具有的力量。在這裡﹐文明所依賴的是技術﹑人的理性和探究的能力以及犧牲的精神。這裡最核心的﹐也是感動了歐洲僱傭兵的是景甜所飾演的新殿帥所說的“信任”的力量﹐這種力量表現得簡明有力。而“磁鐵”所代表的控制怪獸的理性力量也令人印象深刻。饕餮們除了無差別的殺戮和毀滅之外別無所圖﹐正是黑暗和恐怖的隱喻。
片中﹐東方的女統帥﹐雖然超出了中國傳統的限度﹐但卻在當下的隱喻式的狀態下凸顯了自己的某種特異的力量﹐這裡的以“德”化人的表達相對簡單﹐卻也是具有張藝謀式的直接的傳達。如西方人獲取黑火藥的絕密技術﹐成為參與文明與野蠻之戰的關鍵。饕餮具有的不僅僅是攻擊力﹐而且是無所不至的滲透力。從刺殺老殿帥到直接越過長城侵犯汴樑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它們極具危害性。這裡﹐“長城”不僅是抵制外侵的城牆﹐也是中國精神的符號﹐是文明抵禦野蠻的前沿。這裡有個讓人服膺的觀念叫“信任”﹐想得到黑火藥的外國人和中國人之間雖然有諸多的矛盾和問題﹐以及不同利益的糾結﹐但在毀滅性的﹑漫天遍野的怪獸面前﹐卻需要一種共同的合作。唯有信任能超過文明人的唯利是圖和不擇手段﹐才有能力對付野蠻的饕餮﹐獲得生存下去的機會﹐“信任”成為這部電影核心的觀念。中國人之間的信任﹐馬特‧達蒙所演的勇士和中國人之間的信任都是對抗饕餮的巨大力量。雖然文明也有局限﹐但卻最終在與饕餮的決戰中獲得了自己更高的價值。
我們可以看到由於邪惡的無所不在﹐文明的缺陷才能被理解﹐文明的守護才顯得更為重要。這個主題其實是相對簡單的﹐但也顯得黑白分明。在當下的情境下﹐似乎獲得了某種不同的意義。張藝謀用自己一貫的直接性﹐把隱喻做得異常清晰和明確﹐並通過某種文化符號的呈現獲得了一種文化意味的傳達。這種文化意味既來自張藝謀所熟悉的傳統﹐也來自他對當下問題的某種思考後的回應。在世界迅速變化﹐黑天鵝事件頻出的當下﹐直接用全球商業運作的電影方式﹐講出了藝術對當下的一種觀照﹐並在其中努力嘗試進行中華文化精神的傳達。它獨特的拼貼和獨特的故事仍然有其獨有的價值。張藝謀還是那樣猛烈而直接﹐但又讓你被他的力道之大所驚駭。